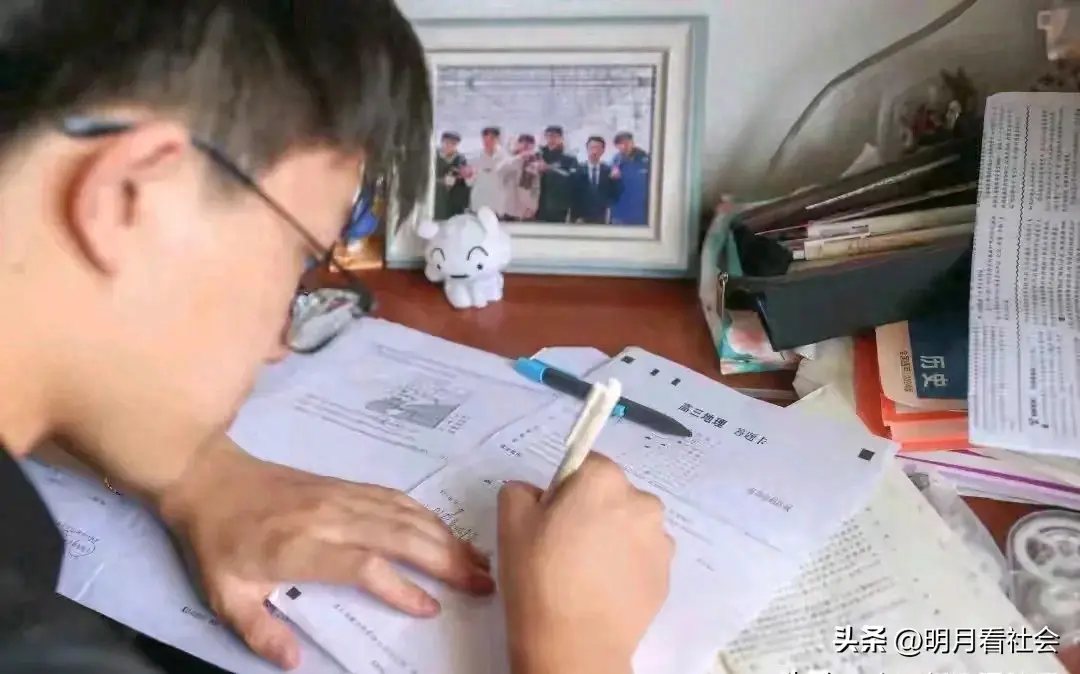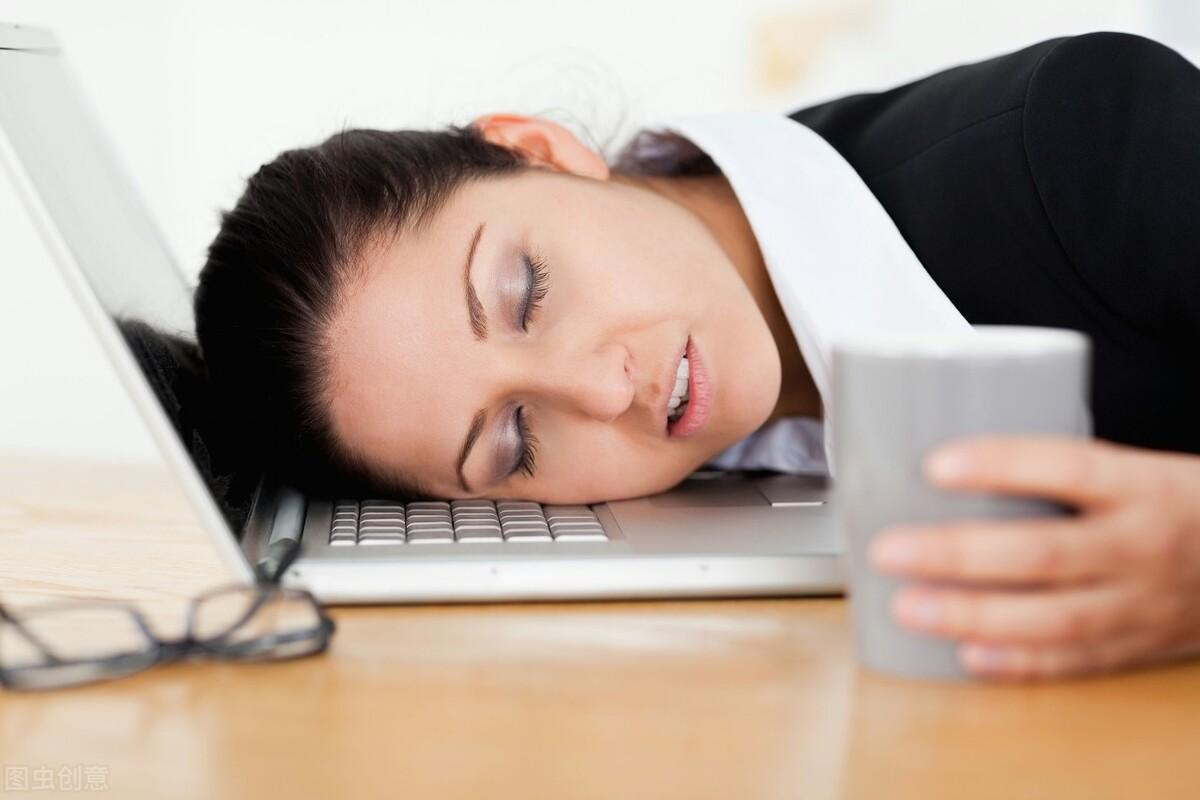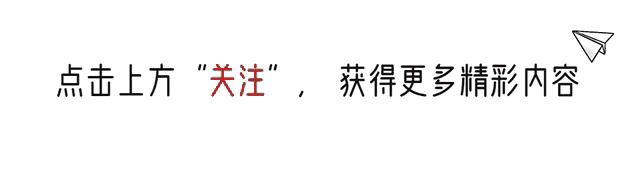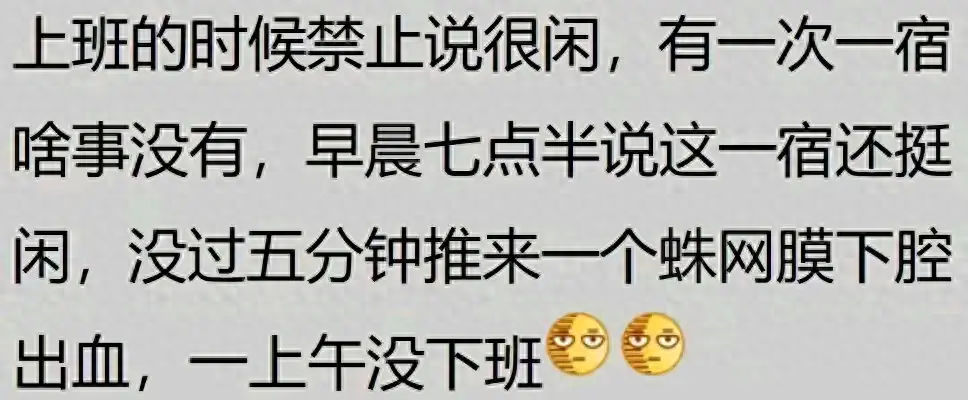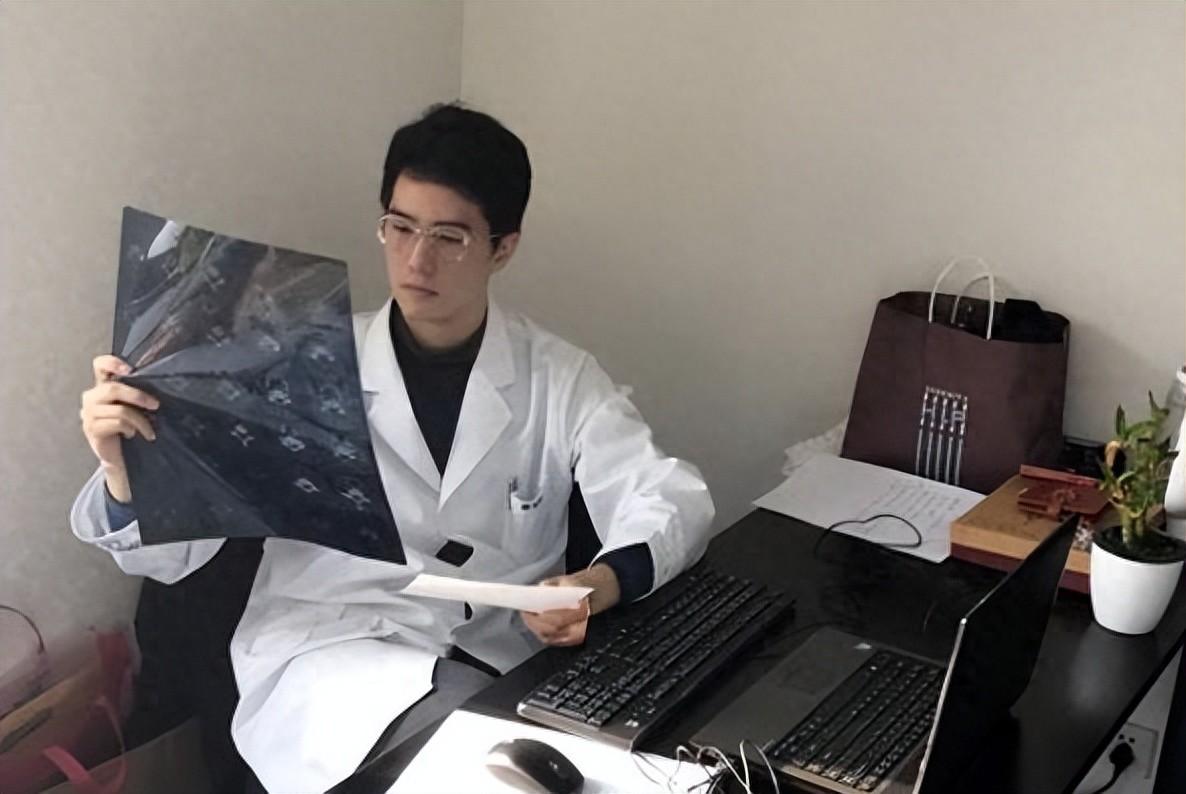著名作家、曾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的萧乾在《我的医药哲学》一书中,分享了他对中医的认识过程,文中描述生动有趣,引人入胜。
“一提医药,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,你究竟信中医还是西医。绝对不相信中医或西医的人我都遇到过,就好像中医个个是误人的郎中,而西医在缝伤口时,必然会连剪刀也一道缝进去……
后来进了洋学堂,每年总是由西医来做体检,阿司匹林又比煎汤药省事多了,……去国七载(按:萧乾曾游学国外,担任战地记者),根本也不见中医踪影,我国传统医学在我心目中,越发没有了位置。
1948年在复旦教书时,一次拔牙感染发炎,半个下巴肿成萝卜,疼痛难忍,那阵子南京路上有的是各种进口西药,阿司匹林不灵,我就拣贵的买,十几天来怎么治也不消肿。
有一天,在教授休息室里,中文系一位老先生见到我那副狼狈相,动了恻隐之心。他问我可相信中医针灸?我捂着腮帮子凄凄惨惨地回答说,只要能消肿,我什么都信。
老先生连衬衫也没让我脱,只叫我挽起袖子,然后打开他那蓝色书包,掏出一个长匣子,里面放着几根银亮的长针。他先在我胳膊上扎一针,问我疼不疼?我摇摇头。接着,他要我张开左手,又在拇指与食指之间扎了第二针。第三针才扎在腮帮子上,进针后不一会儿,折磨我多日的疼痛便霍然而释。”
1956年他陪两位德国诗人在全国各地旅行,刚抵南京,就“大闹腹泻”,“吃了种种药都不见效”。到了上海,朋友安慰他:“请放心,我们这儿有的是进口药。”他“就照大夫的嘱咐服下去。哎呀,不得了,次数加倍了,我几乎离不开卫生间。”
“这时,我想起当年在复旦教授休息室里遇到的那位救星。我向东道主提出,可否让我去看看中医。他们马上就把我送到静安寺路一家不大的医院,好像还不是一家中医院,而只是医院里的中医科。大夫号完脉,开了几味药,另外再加服两粒藿香正气丸。服下去不久,腹泻止住了,很快我就康复了。从此,我对中医佩服得五体投地。” 改写润色: “我想起了当年在复旦大学教授休息室遇到的那位救命恩人。于是我向主人提出,能否让我也去看看中医?他们立刻把我带到了静安寺路一家规模不大的医院,这家医院好像并不是中医医院,而只是医院里的中医科。医生号完脉后,给我开了几味药,另外还建议我再服用两粒藿香正气丸。我按照医生的建议服用药物后,腹泻很快就停止了,我的病也很快康复了。从那时起,我对中医的疗效深感敬畏。”